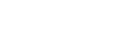捕鸟绳套(回忆我的父亲)
一转眼,父亲的永远离开,
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年了。
父亲(1936-2011),您音容犹存
01 我的父亲,是个“六不像”
我的父亲,生在桂西北一处叫做甫牙的小屯子里,一辈子,几乎都没有离开过那条山沟沟里半步——当然了,也没有来过我现在在顺德的家。
记忆中,父亲到得最远的地方,是到百色起义所在地的百色市城里两次。
一次是给出嫁的大姐购买嫁妆时去的——那里有他的襟兄弟,至今想来已经不记得他给大姐买了什么样的嫁妆,但是他顺捎回来的咸豆豉,晚上炒到锅里时,香味丰盈了整个屯子……
另一次,是我1987年我初中毕业后的一次治病,要到市人民医院里就诊,就是他带的我。只可惜,因为穷,父亲不能呆在医院里继续陪我,也不好意思经常往他的襟兄弟家那里跑,于是,在简单地安排我入院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回了老家,扔下我,孤零零地身在异地他乡……
这个情节,我后来把它放在了《湖南病友》一文中,至今仍然保存在我的剪报集里——这是永远都不能磨灭的记忆。
父亲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按理说,他是个很地道的农民。
可是,认真起来,在我的眼里,他却是个典型的“六不像”。
说他是农民吧,却又背着“缺粮户”的包袱许多年;养着蛋鸭,却几乎很少自己赶集叫卖,即使斗胆一两次,也是需要戴个斗笠,把头埋得很低,生怕别人认出他来——显然也不是个合格的商人;曾经当过民办教师,教过几年书,有些觉悟,后来却坐实了超生户的名声。很多时候,他的手里总有一些缺边缺页缺角的书,比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侠五义》、《小五义》、《七侠五义》、《薛仁贵征西》……(我也因此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地接触了这些经典书籍。)
为了有个瓦房,父亲当起了泥瓦匠;甚至,曾经做过村干部,据说还配过一杆长枪。
父亲还是个猎手,据说是传着爷爷的衣钵。那些年,山上跑的、树上跳的、天上飞的、河里游的、田里爬的,几乎都是我们家的常客,各种鲜美的味道,持续地充盈着我们一家10口人的生活,让我们一家在当年顶着缺粮户的帽子之余,不至于饥肠辘辘,瘦骨嶙峋。
在那个年代,屯子里不少的人家因为常年缺粮,基本都患上了浮肿病,而我们家,靠着父亲的多能多劳,在艰苦的环境里硬生生地活着,而且还很不错——就因为父亲的勤快的手脚,上山下河,让我们尝遍了山珍河味。
有好几次,在他装好捕猎陷阱的第二天早上,他似乎累得不愿再往山上跑了——又或者是想培养我狩猎的技能,就叫我赶紧去查看捕猎猎物的铁夹子,说是爷爷托梦给他,捕捉到猎物了,我兴冲冲地朝着他指点的方向一路飞奔,果然——!
不久,国家禁止了上山捕猎,日渐年迈的父亲于是也就高山仰止,顺水推舟,转往了河里,一边养着10来只蛋鸭以供给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和他的水烟筒,一边临渊垂钓,偶或的收成,也足以让我们一家人在鲜美的河鱼汤里健康地成长……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说山川河水,哺育了人们,可能还有些抽象和笼统;而对于我们一家,正是父亲的奔跑,真正地让山珍河味养育了我们。
每每,望着父亲修整他的捕猎工具,比如铁夹子、捕鸟的细绳套、捕鱼网、鱼竿(还有偷偷地用母亲的缝衣针加工而成的鱼钩),我都非常好奇的或蹲或坐在他身边,眼里满是仰慕和敬佩;而后,目送他怀揣着一家人的渴望,肩扛锄头,腰带镰刀,包裹猎具,踌躇满志地走出家门,看着他的渐渐远去的背影,那感觉,就是我心目中无出其右、无与伦比的侠士与英雄!
02 父亲是个暴脾气的人
我当时不知道,这是否和他因为身兼几种角色却没一个做得好、彼此冲突碰撞有关。如今,在我深入接触了心理学之后,我逐渐发现,这种可能性极大——甚至于对他来说,虽然也许伤害不大,但却侮辱性极强——可怜,我的敬爱的父亲!
记得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发高烧,大半夜的父亲在床上就着煤油灯给我喂药,他似乎担心我不能将整几片药片吞下去,因而事先用勺子小心翼翼地把药片碾碎,和着一点温开水,整成药水,再往我嘴里喂——结果,那阵难闻的苦味,立马肆意地侵犯了我的味蕾,激起我无限的阻抗——于是,我一下子就把满嘴的药水不偏不倚地朝着他干瘦的脸,喷了出来……
父亲顿时火冒三丈,手一挥,把碗往床外地上摔得脆响,反手给我一记耳光,大声吼道:
“不吃拉倒,死了算啦!”
在农村,家家户户都会在中元节期间做生榨米粉,看着新收割大米做出的新鲜米粉,拌着家里刚刚宰杀的项鸡肉汤汁,加以新摘的葱和香菜,那香喷喷的美味,早让人垂诞三尺。
可对于我,却是又爱又恨。
生榨米粉,需要经过选取好米、侵泡、研磨、滤干水、滚圆、煮熟(外层约1厘米的厚度)、打舂、加少许清水搅拌(类如和稀泥,使之成细腻滑软的酱糊状)、分出适量装入透着火柴梗大小筛眼的布袋里,把连着布的上头紧紧捏住,再往一大锅早就沸腾的开水里边挤压边转圈,完毕,再盖上锅盖,而整个过程,大锅底下的柴火烧个不停,这样,丝丝缕缕的米粉线,由硬变熟并很快可以起锅,这样,生榨米粉就算完成了。
生榨米粉的制作,几乎每个环节都有难度,而比较出问题的是在研磨、打舂和挤压(和稀泥)这三个环节,当然,首当其冲是在研磨的时候,如果不小心,磨米的人即使只有区区几粒生米掉入米糊中而没有及时捡出来,那么将影响到后续的打舂、搅拌和往大锅里挤压出米线——你想想,挺着大锅里升腾的热气,还有锅底向上奔腾的火苗,还要用力拧着米浆袋在锅里转圈挤压,是个极费劲的体力活。
记得我们几个兄弟都很小的时候,有几次,父亲仍然舍我其谁地操起挤压米粉的活儿,可是,就因为米浆里有了梗滞(残余的米粒或硬块),瘦瘪的父亲在滚烫的大锅上转了多圈,青筋暴露、汗流浃背却始终挤不出我们全家人期待的丝丝缕缕的粉条,结果,父亲发一声吼,把装着米浆的布袋翻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四周的飞去,直弄得本来乌黑的柱子、碗柜、水缸、土墙等等,一片片惨白,而锅底下的柴火,也被他几脚踢开,四处飞散……
当然,我们也早就魂飞魄散,四处奔逃……
年纪尚小的弟弟妹妹,哇哇大哭——家里,乱了套了……
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经过一番好说歹说,终于请来隔壁的叔叔或堂哥,帮我们继续挤压余下的部分米浆,一家人总算可以过了这个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节日。
大哥同样也是个暴脾气的主儿,可是在父亲面前,永远都只能是小儿科。记得那次,父亲拿出针筒和药剂,准备给家里的病猪打针。当时父亲在操弄着针剂,只见父亲先往药剂瓶口插入一只空针,再用注射器从药瓶里抽出药水……当时大哥好奇,问父亲为什么要先插入一只空针呢?
我当时就想父亲应该会好好解释一下,因为我也有和大哥同样的疑惑。
不成想,父亲头也不抬,大声一吼:
“你以为我笨蠢的吗?”再无他话。
大哥悻悻地走开了,嘴里嘟哝着,却没人听得出说了些什么。
学了物理后,我才知道,父亲真是聪明,他懂得真空和压力的关系,并且运用在生活里——可是,他为什么就不能给大哥解释一下,同时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增长知识的机会呢?
我终于没有问父亲这个问题。直至他永远离开我们。
我是否也害怕得到和大哥一样的境遇和对待呢?
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在记忆里,如此暴躁的父亲,本就是话痨的母亲却从来没有被他家暴过一次。堪称奇迹!
母亲说:“呵!和我斗?门都没有,你父亲呀,看起来凶巴巴,其实也有弱点——那就是,我一发现他真正恼羞成怒,就马上跑开,而他绝对追不上我,也找不到我,要不,我还怎么把你们八个兄弟姐妹带大?嘿嘿……”
至今想来,父亲其实也是深谙心理学之道而且真正运用于他与母亲的互动里,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夫妻关系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对于母亲,更多的只是表象的恐吓,虚张声势,其实哪里会下得了手——要知道,我母亲可是当年方圆几十公里内排得上号的美人,且勤劳贤惠、聪明能干……
03 不要碰我的鱼头!
父亲改从山上狩猎转到河里捕鱼以后,每每煮鱼,一家人早就有了一个约定。那就是,饭桌上,鱼头永远是父亲的“特供”,家里任何人都不能碰。
母亲似乎是帮着父亲给我们带话:作为一家之主,父亲就需要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地“霸着”鱼头,当头嘛,这个权力还真不能让给子女们。
还有一个说法是,父亲平时爱喝几口,有鱼头做伴,吃嘛嘛香,不和父亲抢着鱼头吃,也是孝敬啊。
在我依稀的记忆里,似乎有几次,父亲的鱼头不知怎么的,在准备上桌之前,就没了踪影——这无异乎太岁头上动土,可是大事件哪,怎么得了?
母亲好歹是个和事佬,要不说她自己嘴馋偷吃了个,要不说刚刚不小心被邻居家的猫叼走了……几乎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让父亲在没有鱼头的饭桌上,依然呷着小酒,间或吸着草烟,慢慢地把晚饭吃完。
我当时就想,母亲一定是在遮盖着什么?因为大哥逐渐成年,也早学会了抽烟喝酒,因而偶或斗胆冒险先下手为强偷吃了父亲的鱼头,也未可知……
或者,是其他的兄弟姐妹,觉得鱼头是个解不开的迷,多少都有亲身体验的强烈愿望,所以就“浑水摸鱼(头)”,“嫁祸于仁”,而自己偷着乐一回,也很难说。
倒是我,居然在一次以为有好多鱼的晚上,当着父亲的面,斜拉着脑袋,心怀侥幸地用筷子撕扯着其中一个鱼头……
不曾想,只听见“叭”的一声,我的筷子被妹妹用筷子支开了,她努努嘴,狠狠地瞪了我两眼,咬牙切齿地说:“鱼头是爸爸的。你不能吃!”
父亲这时候也看了过来,我以为将会迎来一阵狂风暴雨、劈头盖脸地斥骂,没成想,父亲这回居然一声不吭,又呷了一口小酒,同时筷子不停,很顺溜地把那鱼头霸到他自己的碗里去了。
我因此基本都没有接触鱼头的机会,而且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想要,越想要——可是父亲却偏偏不给,以至于很长的时间里,我似乎都觉得自己不爱吃鱼头,也不会吃鱼头了。
后来,初中毕业的我在党政机关考到了一份工作,收入虽低却还算稳定,平时也经常参加一些同事、朋友聚会,也终于可以吃到鱼头了——却发现,还是鱼身好吃,肉多,特别是鱼腩部分。
只是,父亲为什么要霸着鱼头呢?
许多年以后,我成了家,并且在被誉为世界美食之都的顺德,经常与鱼为伍,凡逢宴会,必有食鱼,不管焖的、焗的、煎的、滚汤的、蒸的,我终于知道鱼头也只是鸡肋——那上边的肉,实在太少了,还不容易入口,因而都基本避开了它,也终于知道父亲当年为什么要接近吼着让我们不要碰他的鱼头——我的亲爱的父亲!
父亲不让我们碰他的鱼头,让我对他暗生抱怨,嫉妒莫名。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成见。
依稀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在泥泞里看到一支崭新铮亮的钢笔,见四下无人,就慌乱地捡拾起来,擦干净,如获至宝地塞进自己的裤兜里,再一只手紧紧摁住袋口,一溜烟地往家跑,既忐忑不安,又兴奋不已——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学习好帮手啊!
没想到的是,到了晚上,就有人找上了家门,说是我捡到了他们家孩子的钢笔……
记得父亲当时非常生气,暴跳如雷,当着那个人的面,对着我厉声斥骂。
等到那人拿着笔走了,父亲突然间抱紧我,老泪纵横。
父亲说:“孩子,我们虽然穷,但是不能拿那些不是我们的东西,不然,我们就是小偷了;爸爸想想办法,给你买一支!”
几天之后,我放晚学回家,一进家门,只见父亲坐在门口,背靠着门板,笑眯眯地看着我,同时变魔术似的从背后掏出一只崭新的钢笔……
晚上,我偷偷地问母亲,父亲从哪来的钱给我买钢笔呢?
母亲满脸怜爱地看着我,说:“你父亲,今晚少吃六个鱼头啦!”
我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再细问母亲具体是怎么回事。
原来,当天早上父亲钓到了六条活生生的河鱼,回家路上卖给了别人,换到了钱,再跑到集市上,给我买回了这支钢笔……
正是这支钢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学习,勤奋写作。直至参加工作以后,依然笔耕不辍,并有所收成。记得在乡镇政府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月的稿费收入比工资还高,我立马买了两瓶“天成金芝”,专程在一个周末回家,送给父亲和母亲。
再后来,乡(镇)长开始安排我写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材料,并调任我到党政办公室工作。1994年,受聘《右江日报》特约撰稿通讯员,次年,又获评该报优秀通讯员称号;1997年到1999年,我到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现为广西职业师范学院)脱产学习,又凭借一手好文笔和口才——当然还有农村孩子特有的实干精神,分别担任了学院学生会主席、所在系学生会主席,还有院报、广播站的编辑……
从公务员队伍辞职以后,几经辗转,我从广西百色到深圳,再从深圳到阳江,从阳江到广州,最后定居顺德……2006年,远在阳江工作的我,从攒下的工资里,给父亲和母亲寄回了1600块钱,让他们修补了牙齿。
后面,我电话给父亲的时候,问他牙齿是否好使,父亲在电话里显得很开心,说很好哇,都可以嗑花生、啃黄豆和咬排骨送酒咧。
我心下略为欣慰。
想想自己自从20岁参加工作后,和父亲竟是聚少离多,偶尔回去见个面,虽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早知他将要远去,当初为什么不牵着他不放,父子间来十万个一千零一夜?
04 午夜的收音机
当年,邻居一家异姓叔叔因为在村里小学隔壁开了个代销店(小卖部),赚了些钱,买了当时屯子里唯一一台收音机。人们于是经常往那里跑。
那段时间,我对不停断传出说话声还要歌曲的那个神秘的铁盒子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因此经常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去。
盛夏的一个晚上,人们一如既往地,又汇聚到这位叔叔屋子前的平台上纳凉。
不用说,我又跟着父亲去了——我实在是太经不住那些声音的诱惑!
记得到半夜,我被蚊子咬醒了。
睁开眼,我的天,四周黑麻麻一片,我躺的木躺椅也弄得我浑身酸痛……
立即,我打了个激灵:不好,这不是我的家!
“爸—爸——,妈—妈——”我惊叫了起来。
无人应答。
隔了一会,一个嘶哑且带着梦呓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
“啊?谁家的孩子呀?”是那位叔叔的声音。
“叔—叔——,是——我——,我——是——阿——和——”
我既紧张又害怕,语无伦次。
“三更半夜的,你怎么在我家里?”那位婶婶也被吵醒了,嘴里抱怨着……
午夜的收音机
轻轻传来一首歌
那是你我
都已熟悉的旋律
在你遗忘的时候
我依然还记得
父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
原来,当我在附近兜兜转转游来玩去的时候,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先回家去了。而我,却摆了个大乌龙,回马一枪,在那位叔叔的木躺椅上睡着了。
父亲不记得我是否回家,母亲也是——也难怪,他们的孩子太多了,在某个夜晚,多一个或少一个也觉察不到了;而我的兄弟姐妹也是不记得我,姐妹们以为我肯定和几位兄弟睡着了,而我的几个兄弟,要么以为我和另外的兄弟睡了……
而另外的一个尴尬是,据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出生,没有特别指定的接生婆——想想,当年也真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更别说去到医院里生了。而我,是由一个伯母剪的脐带,很不幸的是,这位自告奋勇的伯母弄巧成拙,把我的脐带留得好长。只要我脱下衣服,那个脐带就像半截肠子一样,在肚脐眼那里往下耷拉着,就像尿尿的“小鸡鸡”……而屯子里的好事者,经常拿着我的肚脐取笑,甚至追着我,两只手上下比划着,扬言要“阉割小鸡鸡……”吓得我好长时间不敢出门。也几乎从来不敢和伙伴们去河里游泳——事实上,我童年的记忆中,家里本来就有不少的尴尬事发生,而这个肚脐问题更是让我几乎完全封闭了自己,以至于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好伙伴——这在很大程度上,深埋着的懦弱与自卑,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人际关系发展,也暗示了和暗示着我的成长之路何其坎坷、折腾与挫折……
还有一件事,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对父亲心怀不满。
在我们农村老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本叫《八字命根》的用宣纸线装而成的册子(很多人也叫家谱)。上面记录着一家人的出生年月日,还具体到时辰。谁家的孩子出生了,就请上屯子里有点威望、人品好、有文化的老人用毛笔在这本册子里记录下来,算是添丁了,发财了。
而对于我家,在那本家谱里,一家大小——我的父母亲、大姐、二姐、大哥、二哥、三妹、四弟、五弟的出生年月日和时辰都清清楚楚地录入了,唯独——没有总排行第五、兄弟排行第三的我——
是的,我没有在我家《家谱》的收录之列!
母亲后来很多次对我说,因为孩子确实太多了,照顾不过来,偶或的遗忘,也很正常。
只是,在我的潜意识中,从听收音机、肚脐眼和《家谱》这三件事中,我发现我自己是被忽视、被嫌弃甚至被抛弃的——这种童年的创伤,一直伴随着我,尽管历经风雨,逐渐成长,也难以忘怀。
心理学上说,凡是童年失去的,都会在成长后找回来。
这种缺失的刻骨记忆、未完成事件的压抑情结,在我后来的学习特别是人际关系和实际工作中,持续次第地呈现。回首过往,至今,我一直在寻求被关注,被接纳,被重视,被听见,被理解,被认同,很难接受延迟满足。当遇到不懂自己,不关注自己,不接纳自己,不重视自己,不理解自己,不认同自己时,我就会很烦躁,就会马上表露出很大的情绪抵触乃至行为对抗,最终只能自己吞咽苦果——甚至,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我的人际、学习、工作、婚姻与家庭。
我因此费劲折腾,也不停地变换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压根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而当我逐渐深入接触心理学并因此走上培训讲师之路,我发现我自己在讲台上、舞台上的挥洒自如、出口成章、娓娓道来而引来掌声不断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我这正是在找回我童年缺失的部分——我需要越来越多的人都看着我,都听我说!
否则,我就会复发咽喉炎,时常干咳,或感觉胸闷、心慌、呼吸急促、说话结巴……
有几次,就连经常翻看心理学书籍的小女儿也说,“妈,爸爸经常干咳,心理学上说是他的内在是希望世界看着他,听他说……”
不久前,我给母亲打电话,又说到《家谱》的事。母亲在电话里跟我说,父亲卧病在床后,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绞尽脑汁、穷思其想,并多方寻证,终于在家里的八字命根谱上加上了我的生辰八字。
也就是说,父亲在他临大去之前,把我录入了《家谱》。
终于——我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根”!
05 我要坐一次火车
得知父亲卧病在床的消息,是2011年的父亲节前夕。
那时,我的小女儿才出生约6个月,而我也从原来的单位里辞了职,正在寻找另外的工作。而在老家,大哥和二哥开始起楼房了。此前,父亲征询我,是否要留一块住宅地?我几乎不假思索,婉拒了父亲。我说,让大哥、二哥的房子宽敞些吧,我打算一直在广东发展了……
那时候,依稀记得父亲似乎沉默了很久,后面长叹了一声,就把电话挂掉了。
过一段时间,像以往那样,我又拨打了老家里的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是母亲。
突然间,我内心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和母亲聊些话,接着就找父亲。可是,在电话那一端,母亲似乎迟疑了一会之后,才用一种低沉的语气告诉我,父亲因病躺在床上,不能自个起来,已经很多天了……
这真是晴天霹雳!
接着,从母亲的嘴里,我陆陆续续地知道了父亲病躺在床的原因。
我知道,再多的对外的抱怨,也已经无济于事。
我自己身为父亲的亲生骨肉,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居然没有在他身边,一则及时施予援手,二则给予应有的慰藉……
我想,如果我当时在家,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呢?
只是,时间没有如果,只有果如——因果的轮,在转着。
很快,父亲节的那天,我又给父亲打了电话,我告诉父亲,祝他节日快乐!
电话里,父亲愣了片刻,笑问我是什么节日?我说是父亲节呀,是您的节日。
说着说着,我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父亲在电话里安慰我,说傻孩子,哭啥咧?
2011年,父亲节的记忆
……
和许多家庭一样,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长大成才,光宗耀祖。
只是,就在他的一生里,我们五个兄弟基本毫无出息。用俗话来说,是“农”字当头,吃喝犯愁。虽然,在兄弟间排行老三的我,在1992年参加国家招干考试当了一名国家干部,多少也算给他撑了些面子,嗓子也比之前响了许多,让他在人前人后颇为自豪——只是,到2002年,也是父亲期待我十年磨一剑在体制内稳步提升之际,我却“独狼”式的辞职下海,而且没有和他、母亲或亲友打一声招呼,让他从此萎靡不振,终日烟不离手,酒不离口……
几经波折,我从广西来到了广东,过深圳,下阳江,上广州,最终在远离故乡千里之外的家电之都——顺德,把家安置了下来。
那时侯,我还没买自己的小车,但父亲知道我在顺德定居之后,眼里闪烁着希翼,嘴里说:“我至少要去你那里一次,坐火车去。”
顿了顿,父亲又说:“我这辈子,还没有坐过火车咧……”
父亲终于没能坐上火车,也没有来过我在顺德的家一次。
不仅如此,就连我自己购置的小车,他也只是可能在照片里见过,更别说坐了。
倒是在他生病的晚期,在大哥的指引下,父亲坐着我从亲戚那里借来的面包车,去了当地北部山区凌云县逻楼镇一处偏僻的山洼里寻访大哥无计可施之余经人介绍的一个土医。
那是火热的夏天,是父亲去世前几个月的一天。那天晚上,我们父子三人住进了一户人家。在我和大哥与土医一家人共进晚餐的当口,父亲却需要配合土医开具偏方的需要,在喝下两大碗不知是什么药水之后,一个人躺在床上,从头到脚蒙上两床厚厚的棉被,说是要经过出汗逼出父亲身上的毒素来……
可惜,我坐在摆满了肉菜的饭桌前,听着父亲因为闷热难忍而发出的阵阵呻吟,恨不得立即过去掀开被子,痛斥土医一顿,然后走人。
可是,看着大哥一脸淡定,特别是他对那位土医的虔诚与敬重,我按住了自己的冲动。心里想,正规医院经过综合会诊,已经向我们做出劝退回家的建议,而现在大哥听人说这位土医神乎其神,声名远扬,不如姑且看看,万一——妙手回春呢?
父亲的呻吟,停停歇歇,断断续续,却一声比一声绝望和悲凉——我的心,都快碎了。
不知什么时候,感觉是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只听得那位土医和大哥说着话,大意是父亲的病已进晚期,加以今晚怎么弄,都排不出汗来——对此,土医自己也无能为力了……
一夜无眠。
第二天清早,我们无奈回归。
途中,在一处上坡的急拐弯处,因为速度过快,车子差点“漂”向悬崖边,吓得我大热天的也冒出一身冷汗。
而在那一刹那转头瞥向横躺在后排的父亲,我既深感内疚,更悲愤不已!
“父亲,凭我的车技,我可以把你安好地护送到家——可是谁的医术,又能给我们一个共同的未来??”
无人应答。
06 让我再看你一眼
从土医那里回家后的第二天,父亲似乎突然比以往精神了许多,说话清晰,表情兴奋,目光四处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又像在想着什么,说着什么。
在那个时候,我甚至认为父亲会因此改写自己的命运,从病痛中奇迹地恢复过来——其实,后面我知道,当时只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现象,在父亲心中,还有未完成的事件,让他牵挂不已。
我当即陷入了沉思——究竟,是什么,让父亲如此这般牵肠挂肚、魂牵梦绕?
往事如潮,在一刹那间涌进我的心头。同时,也启动了大脑雷达,努力搜索父亲还有哪些未曾实现的心愿?
父亲辛辛苦苦一辈子,养育了我们八个兄弟姐妹,虽说没有大富大贵,但个个都成了家,儿孙满堂,总算孝敬有加,勤劳肯干,遵纪守法,健康成长。这些,父亲应该不用担心。
彼时,大哥和二哥正在建楼房,之前在通电话的时候,总听见父亲乐呵呵的笑声,母亲说他一点都不嫌自己老,整天忙里忙外——虽然,基本都请了很多人帮手,但父亲依然从不缺席。
父亲对建新房子的接近偏执的爱,让我猛然想起我们小时候的曾经的家:
遥想当年,我们年久失修的茅草屋,在多少个暴风雨和雷鸣电闪的夜晚,全家人听着屋顶上被风掀翻的一排排茅草,在屋子里四处找寻不曾漏雨的地方,慌慌张张里挤成一团,个个心惊肉跳,彻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一家大小鱼贯而出家门,上山割了茅草回来,再搭上梯子,及时填补屋漏。
之后,历经波折勉强翻新后的瓦房,也因为省着瓦片,在盖瓦时摆得稀稀疏疏的,分量自然不够厚重,在狂风肆虐和暴雨侵袭的夜晚,听着瓦片被呼啦啦地刮走,或直接掉到阁楼上地面上,吓得我们战战兢兢,恐怖至极,想想,要真有地洞,多好,不用担心风急雨骤。
突然间,我心头涌起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是房子?”我在心底里叫了起来。
果然,沉静许久,父亲说:“两个房子都建好了吧,我想再看看,可惜,我走不动了……”
我们都明白了——父亲需要他的几个儿子,背着他,再看看正在建设中的新房子。
这时候,平时强硬、霸道甚至有些蛮横的大哥居然哭出声来,转身走开了,他不忍背着父亲,或许他早有预感——这将是作为长子与生父的最后的合作。
二哥呢,因为一些原因,不方便背,而且可能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赶着建造房子的事,已是一身疲惫,特感无力。
我因此有了背负父亲实现他最后心愿的机会。而这,也算是我多年未曾亲近父亲、尽到自己赡养父亲的责任的补偿么?!
几乎没有思索片刻,我蹲下身,由大哥、二哥扶起父亲,并托到我的背上。
感觉好轻啊!——我的瘦骨嶙峋的父亲,身高1.7米多的曾经的真汉子,风里来雨里去的好猎手,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此刻,就趴伏在我的背上,像一个刚从前线受伤回来的战士,在退回后方之前,还再看一眼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土地……
我背着父亲,托着他枯瘪而僵硬的身躯,慢慢地爬上楼梯,大哥和二哥紧跟着在后面,适时地协助扶着父亲,不至于他搭着我肩膀的双手感觉太使力。
母亲也加入了进来,一边嘱咐我小心迈步,留意脚下可能的铁钉、砖块或其他障碍物,一边当起了导游,告诉父亲哪里施工完成了,哪里非常结实,用了什么材料,还有哪些材料正在路上,多长时间就可以运到家里来……
我们一行先从大哥的房子出发,再到二哥的房子,踏上到每个楼层,穿进每个房间,还上到了楼顶天台,向着东南西北驻足眺望……
当我还想背着他继续走出楼房外,想让父亲回望自家在建楼房整体样貌的时候,父亲吃力地说:“累了,不看了,我们回家吧……”
“好,我们回家……”我应着父亲;眼里噙满了泪水,依依不舍地把父亲背回了他的房间。
回头走出房间,进到二哥的房子。
母亲声音哽咽:“这是他的命啊,辛辛苦苦风风雨雨一辈子,房子都准备建好了,人却要走了……”
我无言以对。
一会低着头,不让母亲看到我的哀伤;
一会又仰起脸,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终于,还是忍不住——只好,跑到水龙头边,飞快地用水冲洗自己的眼和脸。
次日,我就匆匆地赶回了顺德。
其时,我正纠结于继续打工或自己创业,心下焦虑,也因此没再能多陪父亲。
日子,在忐忑不安里延续……
距离开老家不过十来天的光景,在一个心情恍惚的上午,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
我一看,是老家熟悉的电话号码——
父亲病情趋危,希望所有的子女都尽快回去看他啦!
放下电话,向老师请了假后,从学校里接出大女儿,告诉她:“爷爷病危了,我们尽快回老家去……”
大女儿“哇”地一下哭出声来:“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将不在——我心底里,涌起一阵阵悲凉……
妻因为要照看未满6个月的小女儿,不能一起踏上归程。为确保安全,我决定不开小车,而是和大女儿挤上了长途客车……
一路颠簸之后,我们匆匆地跑进父亲的房间,大白天的,虽然亮着灯,但房间里很是阴暗,空气里夹杂着汗水、药水和一股发霉的味道……
可怜的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几乎是动也不能动了。
我欲哭无泪!
07 最后的遗产
2011年7月11日,父亲静静地躺着。
其时,他的八个子女(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已经挤在他的床前了。
我们默默地守护着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轮着用棉签给他干涸的嘴唇点水,还不能染水太多,父亲不喜欢把水弄到他的脸上、脖子上,那样会让他感觉很不舒服。
过了些时候,父亲突然说话了,叫大姐到坐到他身边。
大姐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显得很淡定。
大家静静地坐着,都没有说话;我强忍着眼泪,心绪千结。
“喏,这—辈子,我—没有—什么—财产—给—你们……”父亲有气没力地说。
“我身上还有72块钱。”父亲使着力,继续说。
“你们母亲、大姐和二姐—辛辛苦苦—帮助—养育你们—几个弟妹,不容易,她们—每人—10块,你们—六个弟妹—每人—7块—”
等到我们一一收了钱,父亲又说了:
“我—走后,你们—几个—兄弟—姐妹—要—团结,要—好好对待—你们—母亲……”
大哥哭出了声,突然跑出了父亲房间,甩着手,在客厅里来回不停地走。
我们几个也差不多都哭出声来……
大姐说:“弟妹们,不要哭……不要哭……”
而她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
永远的711
下午2点10分,父亲喉咙里发出“咯”的一声轻响……
“我们的父亲,走了……哇……”大姐哭出声来了!
顷刻间,房间里哭声一片,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抑制我们的悲伤了。
……
说来奇怪,就在父亲入殓的时候,晴空里突然想起几声响雷,紧接着下起雨来。
我惊愕了。
是父亲的走,真的惊动了天地?
抑或是我们的不孝,上苍给予的斥责之声?
无论如何,我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这个时刻。
父亲走后的那些天,我和母亲唠起家常,自然少不了父亲。
母亲说:“别太难过了;好歹,你当初给你爸整了牙,要不,他可能还活不到今天咧。”
多年以后,小女儿经常念叨:“爸爸,我一眼都没见过爷爷,很不公平,我都不知道他长怎么样?”
我把截图后的父亲的照片给她看,小女儿左看看,右看看,问我是否还有别的,我回说没有了,这是唯一的一张。
我的父亲
小女儿沉默了;良久,她突然叫了起来:
“爸爸,怎么回事,你和爷爷竟然连一张合影照都没有!”
我转过身,避开女儿,跑进房间,双手掩面,泣不成声……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
父亲,你在天堂里还做生榨米粉么?那味道怎么样?
父亲,天堂里也有火车么?你坐了么?感觉怎么样?
父亲,你还会对我当年从公务员队伍辞职耿耿于怀么?
父亲,天堂里有收音机么?是否,也在播放着——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 分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