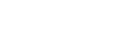死水闻一多诗原文赏析三美(论新月派主要诗人对闻一多)
原创文/董元奔
[摘要] 针对新诗发展之初出现的泛情和白话淡而无味的现象,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提出将诗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作为新诗创作的原则,并亲自进行创作实践。该派其他诗人徐志摩、朱湘自觉实践闻一多的理论主张并为“三美”诗论注入新的血液:徐志摩将性灵美注入“三美”,朱湘将民歌美注入“三美”,从而使新诗在一定程度上既节制了情感又艺术化了白话。
[关键词] 音乐的美 绘画的美 建筑的美 性灵美 民歌美
中国新诗诞生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洪流中,但是,它在晚清时就已经开始孕育。19世纪后期,狭隘的复古主义诗歌创作思想统治诗坛。以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提倡诗的“杂凑模仿”,认为拟古是诗的“通于大道”;同时期的“宋诗派”和稍后的“同光体”诗人则主张模仿江西诗派,以考据逞才学,大量用典,制造僻词。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无病呻吟之作充斥诗坛。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渗透的程度越来越深,这种无病呻吟之作越来越脱离现实,一场深刻的诗歌革命终于爆发。1868年,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后又要求诗歌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梁启超相应黄遵宪,发动“诗界革命”,要求诗歌要具备“新意境”、“新词语”。黄遵宪和梁启超的诗歌改革主张直接启迪了胡适对“新诗”从内容到语言上进行彻底革命,1919年,胡适在总结自己的新诗创作“尝试”的经验后发表《谈新诗》一文,“新诗”这一文类正式诞生。
《谈新诗》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强化了新旧对立的意识形态,使新内容(时代精神)和新语言(白话)称为新诗的指标。随着胡适式的新诗尝试之作的不断出现,诗质的丰富性逐渐被滥情取代,诗歌语言的凝练性逐渐被白话的透明性取代,诗的美学色彩越来越淡,一时间,白话能不能入诗的疑虑笼罩文坛。为了克服新诗的滥情倾向和改造白话,找到成熟的新诗创作道路,现代诗坛先驱们开始了继续探索。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均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提出“新格律诗”理论,即要求新诗具备“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这里,我就谈一谈新月派主要诗人是如何实践“三美”诗论并使之不断丰富而成为改造新诗创作幼稚病的一剂良药的。
(闻一多画像)
一、闻一多提出“三美”诗论并努力实践
在新月派诗人中,闻一多的文艺观独树一帜,他的新诗理论涉及两方面,一是在内容上强调诗歌对生活的把握,二是在形式上既要有内在的幻想的情感又要有外在的“合规律”的模式,这“合规律”的模式就是“三美”原则,即新诗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
“音乐的美”,是新诗格律的第一个内容,主要是指诗歌的节奏美。闻一多非常重视诗的节奏,把节奏看作新诗格律的核心,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说:“格律就是节奏。”他认为,诗是从生命中产生的,而生命的节奏是无处不在的,因而诗的节奏也应是无处不在的;诗是从生命中提炼出来的,它高于生命,因而诗的节奏比生命的节奏更强更明朗。为此,他批评郭沫若的作品一味宣泄自己的情感而忽视了诗的节奏,他认为郭沫若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他违背了生命的节奏规律,因为生命并不总是绷紧的情感的弦。在具体谈论诗的“音乐的美”时,闻一多认为诗的节奏包括外在节奏和内在节奏,外在节奏主要表现在音尺、音节和用韵方面,内在节奏主要表现在字句在组合中所体现的情感的波动以及在旋律中所显示的思想起伏状况。请看闻一多的名作《死水》第一节: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每句诗均由二音尺和三音尺构成,且二音尺和三音尺的搭配规律也是一致的,调和的音节是字句整齐,用韵虽然很规范但并没有因为挑选汉字而损害句意;同时,四句诗就像我们在踏步,又像心脏在跳动,诗人对祖国现实的不满和无奈便随着我们体会到的生命的律动传到我们的心里。古人早已指出,诗与乐是不分家的。笔者看来,诗歌之所以有美感,正是因为它的音乐性从大方面暗合了大自然的节律,从中的方面暗合人们从事社会活动(劳动、祭祀、娱乐等)的规律,从微观上暗合了人体的节律而使“人体深处”的情感以一定的节律传达出来;诗歌的语言之所以能“绕梁三日”而余味不散,关键也是在于诗歌语言的音乐性,所以白话具有了音乐性就具有了韵味。
“绘画的美”,是新诗格律诗的第二个内容,主要是指诗的词藻美。闻一多从苏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出发,认为诗画同源。画以色彩、线条构成视觉形象,欣赏者凭感官直接把握;诗以文字组成清晰生动的生活场景,欣赏者凭想象力复现诗中的生活场景。闻一多认为诗画相同的契合点是“通感”,即通过联想和想象让各种感官相互作用,从画的直观场景过渡到心中成为有情味的活动的场景,从诗的“象形”文字层面和其中蕴含的情感内涵过渡到画的线条和色彩层面。套用王国维关于“隔”与“不隔”的论述,我们认为,表层的“隔”经过欣赏者的想象可以转化为心理深层的“不隔”,同时,这也使简单透明的白话平添无穷韵味。闻一多在批评郭沫若的作品时指出,《女神》中夹用了一些西洋音译文字,这些音译文字不像汉语文字那样具有象形的色彩美,象一个个“变形虫”,妨碍了诗向画的转化(闻一多《泰果尔批评》)。《死水》用词极富色彩美,尽管诗写的是丑和恶,却色彩艳丽鲜明,反衬丑恶,强化病态美对否定现实的力度,“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这四句诗中包含了多种颜色:黄色的铜、翠绿的翡翠、黑色的铁罐、粉红的桃花、暗灰色的油腻、浅灰色的罗绮、或灰或白或灰红的云霞,各种颜色杂凑在空间狭小的臭水沟里,使得这些颜色成为丑恶事物的装饰。
“建筑的美”,是新诗格律的第三个内容,主要是指使得文字在空间感方面要做到“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诗的格律》)。写诗就像做菜,一道好的菜肴不仅要有“香”和“味”还要有“色”,好看是引起食欲的第一关,一手好的诗不仅要有音乐性和色彩感,还要有外观即句式上的美感,好看是引起读者欣赏欲的第一关。闻一多要求新诗要分行写,这一方面使诗从直观的形式上与散文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也使诗给人一种合规律的层次分明的格式。古代的格律诗律诗绝句句式整齐,古风句式随和,律诗绝句在抒情上就比古风有节制。分行写的“均齐”的句配以“匀称”的节本身就是一种“束缚”,既从内心节制情感的泛滥,又从表达层面上设置第二道“绊马索”防止表达的过程中情感得不到节制。郭沫若的早期作品固然也是分行写的,但是每句字数多则十几少则一二,每节句数也是多则十几少则一二,闻一多批评这种大开大合的句式,认为正是这样的句式导致了情感的过份宣泄,损害了诗的美感。闻一多在谈诗的“建筑的美”的时候进一步指出,“建筑的美”应该与诗的精神相调和,并“根据精神制造成”(《诗的格律》)。还看《死水》这首诗,全诗五节,每节四句,每句九字,整齐划一,但是,朗读这首诗,并不感到呆板单调,由于诗的内容是抒发强烈的爱国精神,整齐的句式配合有节制的韵律,回环往复,曲折有致,声声紧催,步步紧逼,诗人含泪的爱国之情一路飙升。当然,闻一多时代和以后的新诗发展在句式处理上并没有完全做到整齐划一,这是因为过分讲究句式的整齐不仅在形式上削弱了对旧诗革命的成果,而且不利于有些感情的抒发。闻一多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创作实践中适当的诗句式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
“三美”诗论是针对新诗的诗情泛滥和白话缺乏意味而提出的,目的是给新诗带来艺术价值的提升。闻一多认为,一手成功的新诗作品应该是“三美”熔铸为一体,既不能分割开来也不能偏于某一方。
(徐志摩塑像)
二、徐志摩为“三美”诗论注入“性灵美”
“新月派”另一位代表诗人徐志摩是一个天才诗人,他以自己丰润轻灵的笔在新诗坛上把自己塑造成情与美的诗歌王子:美的追求,灵的向往,爱的灌注,鲜亮的理想,超脱的姿态。徐志摩的成功是与他自觉接受闻一多“三美”诗论的“束缚”分不开的,不过他把自己天才诗人的主要基因“性灵”灌注到“三美”中去了,使“三美”成为徐志摩的“三美”,成为更完善的新诗创作理论。所谓“性灵”,是指充满灵气的玲珑剔透的性情,它有着飘忽不定的空灵感。
徐志摩早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读了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大量作品,信仰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崇尚爱、自由和美,因而他早期的诗自由洒脱,充满性灵,但情感过于泛滥,许多作品表现个人理想主义的狂热,缺少诗质,一些表达爱情的作品也过于一览无余,诸如“别拧我,疼”,“我的爱:再不可迟疑”这样的句子。回国后,诗人尝遍了爱情和生活的苦恼,其个人主义理想被现实撞得粉碎,他开始有点深沉,他的激情受到约束,特别是在新文学活动中认识了闻一多之后,他的诗歌创作开始成熟。他从闻一多的新个律师理论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猛虎集》序言中,徐志摩说:“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们好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是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才憬悟我自己的野性;……”闻一多给予徐志摩最大的启发就是通过“三美”来束缚他的野性和凝炼他的语言,同时,徐志摩诗歌创作方面的优点特别是他的性灵美也完善着“三美”诗论。
首先来看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的美”。闻一多诗歌的音尺整齐规范,用韵严格,诗人的思想感情有节奏的跳动着,读闻一多的诗就像
一支进行曲;徐志摩把性灵美注入诗的节奏中,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闻一多进行曲的节奏,进行曲变成了小夜曲,音尺规范中有变化,用韵轻盈灵活,叠音词和助词“的”“了”的运用使节奏更加轻巧 ,这样,徐志摩诗歌的节奏就呈现出适度的灵活性,比如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首节: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这首诗就这样开始了,诗人的性灵使诗像一渠春水欢唱起来,其音节的波动性和柔和的旋律一下子就引起读者的心灵震动。我们分析一下它的音尺组合规律就明白它的节奏之妙了。 每句由一音尺、二音尺和三音尺组成,音尺类别比闻一多要多;第二句比其他三句多了一个一音尺,四句的音尺组合比闻一多灵活。而《再别康桥》全诗七节,每节的一三句和二四句分别有着相似的音尺组成;诗的最后一节改变了几个字,和第一节基本一样,其音尺组合只在第三句上有一点改变。这些,都使节奏在轻巧中显出抑扬顿挫的变化。徐志摩在《诗刊放假》一文中说:“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称与流动。……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诗的真正的趣味。”可以说,创造性地实现了闻一多的“音乐的美”,是徐志摩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再看徐志摩诗歌“绘画的美”。由于生活经历和思想取向不同,闻一多的诗多批判和讽刺现实,诗歌中的颜色要么发暗要么以鲜艳的复色(即混合色)反衬现实的阴暗,因而其色彩给人以一种压抑感;徐志摩生活在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又过早地接触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化,情感热烈奔放,热爱大自然,作品中的政治色彩和社会色彩较淡,因而诗歌中的颜色很单纯,金碧辉煌,明丽光艳,让人赏心悦目。徐志摩做到这一点真是因为他的“性灵”穿行于闻一多的色彩中,使沉闷的色彩能够透气和达到空灵。《再别康桥》像一幅赏心悦目的水彩画,诗人用语言的彩笔向读者展现了康桥的旖旎风光:四五月间艳丽的黄昏,夕阳的余晖把康河边的垂柳镀上一层金色,柳条儿那婀娜多姿的身影倒映在波光潋滟的水中宛如娇艳柔美的新娘;康河的水波里散布着绿油油的水草,它们随波起伏摇曳,好像在向我挥手作别;彩虹透过康河上游深绿的榆树,照到树下清澈的潭里,彩虹与潭水搅合在一起,潭中五色斑斓,梦一般幽美;而如果早上划一叶小舟,划破霞光彩虹,划进青草深处,可以找到青春的梦想,晚上归来时,满载一船星辉,会禁不住放声歌唱……康河的风光在诗人的笔下是五颜六色的,是透明得可以相互渗透的五颜六色,这透明,正是诗人的性灵融进大自然的结果,正是诗人灵动的对大自然、对康桥的赤子之情流出笔端的结果。
最后来看“建筑的美”。闻一多的诗讲究“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整首诗在形式上像一幢没有窗子的摩天大楼,徐志摩把性灵美注入“建筑的美”之后,他不让诗歌在外在形式上齐刷刷的拔地而起,他做到了节的基本匀称和句的基本均齐,使闻一多的摩天大楼开了许多窗子,新鲜空气透进去了,污浊空气散出来了,读者的身心得到疏导。《再别康桥》每句诗的字数只是大体一致,每节四句故意以相同的参差状态排列,这些一方面从直观上显得错落有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读者体会到诗人里看康桥时一步三回首的依依不舍之情。
徐志摩把性灵znuru“三美”,使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理论既关注了对新诗滥情的束缚,又没有忽视对诗人纯真情怀的青睐,从而使新诗获得了自然的生命力,使古典诗歌的弘扬生命的精神内涵复活于新诗中。
(朱湘照片)
三、朱湘为“三美”诗论注入“民歌美”
朱湘也是新月派诗人,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他和徐志摩一样,在创作中努力实践闻一多的“三美”诗论,他也和徐志摩一样,既看到了 “三美”诗论在纠正新诗滥情和白话无味方面的现实作用,也看到了“三美”诗论在指导闻一多本人创作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那就是使对感情的过分束缚和诗的语言模式的呆板。徐志摩用性灵美来弥补“三美”的不足,朱湘则把民歌美注入“三美”中。
朱湘首先关注的是民歌的音乐性。一首民歌是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数百年才广为人知的,是在成千上万老百姓不断传唱的过程中成熟的,因而,音乐性,极强的音乐性是民歌的命脉所在。朱湘把民歌的音乐美引入新诗创作,通过句式的相对灵活、短短的音尺、大量的重章叠句、大量的句中感叹词和语气词运用等使作品节奏自然,情感清新,普通的大白话变得情趣盎然。请看《采莲曲》中的一节:
小船呀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娇娆。
这分明就是在唱歌,很短的音尺像是踏步,每句中的助词“呀”不仅调节了节奏而且增添了亲切感和朴实感,我们朗读这样的诗句就好像欣赏一个水乡姑娘一边扭着身子摇船一边趁着扭动的节奏唱山歌。词主要是因为西北民间音乐燕乐的演唱需要而产生的,因此,词虽然以文人创作为主,但它们大多清新、明朗、通俗,民歌味非常浓。朱湘有意识地把词的句式运用到新诗创作中,强化新诗的音乐性,《采莲曲》接着写道:
日落,
微波,
金丝闪动过小河。
左行,
右撑,
莲舟上扬飞歌声。
歌声随着上下飘动的莲花舟抑扬顿挫。虽然这六句诗每句字数相差很大,但它们绝不像《女神》里的句子,六句诗分成两个句群,每个句群简直就是半首“如梦令”,由于借鉴了词的句式,虽然长短不齐却符合音乐的高低、疾徐、长短、刚柔,因而琅琅上口,流转如珠,两个“半首”组合在一起形成广泛意义上的重章,回环往复,读者就随着莲花舟深一桨浅一桨,伴着少女的歌声漂向遗忘了很久的遥远的故乡,漂向童年。民歌美的注入,使闻一多的“音乐的美”贴近了老百姓的情感和老百姓的语言,老百姓的情感及不会掩饰又不会无病呻吟和泛滥,老百姓的语言并不能仅仅理解为白话,而应理解为真实的和活着的语言。
朱湘也力求使民歌美与“绘画的美”相结合。如果说,《死水》给我们提供的是一幅静止的油画,那破铜烂铁,那铁罐上的桃花,那绿酒似的死水,那白沫,等等,它们以特定的空间组合构成静态的图景,诗人和这样的图景构成静态关照关系,那么,朱湘把民歌美注入这幅画以后,静态的图景就变成了电影,画面动起来了,成为真正的有声有色的生活,我们看不到诗人,只看到流动的生活,并依稀感受到诗人流动的感情。请看《采莲曲》,作者用民歌中最常用的白描的手法描写道:绿色的荷叶,田田的,一眼望不到边,落日的余晖洒在荷叶上,荷叶的绿色透出朦胧,落日的余晖洒在荷叶间的水面上,水面上泛起紧邻般的光,半开的荷花招引成群的蜂蝶,一叶采莲舟在荷叶丛中左一桨右一桨的穿行,摇桨的姑娘身着鲜艳的服装,她因憧憬心上的人儿脸颊上泛起榴花一样的红晕……这不是一个一个的色彩片断,而是流动的采莲生活,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接触不到的最朴素、最鲜亮、最空灵的生活。朱湘之所以能把生活中的颜色处理成流动的艺术色彩,是因为他已走出闻一多和徐志摩的抒情模式,他主要就是要描写生活,情感潜流在生活中;他让读者沉湎在他的艺术境界里流连忘返,让人们的心灵在他的审美世界里获得自由,读者接受了作者的关怀却不知不觉——读者和作者的情感在流动的艺术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交流着。
那么,民歌美是怎样被朱湘用到“建筑的美”上的呢?闻一多的诗在外形上是摩天大楼,徐志摩用性灵美为之开了窗子,朱湘则用民歌美从两个方面改造这种建筑美。第一,朱湘对于诗的句式的组织与排列与徐志摩相似,整齐中呈现规律性变化,但是,他把民歌美引入创作中,就使这种“建筑的美”增添几多艺术张力。《采莲曲》大量使用农村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或现象为这所房子粉刷上极具春天般感觉的内墙与外墙涂料,如用荷花比喻少女的美丽,深藏藕中的藕丝比喻少女的羞涩,用莲蓬子多双关少女的怀春,用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美化人间生活,等等。第二,民歌美使朱湘的诗在外观上成为“海市蜃楼”,眨眨眼仔细一看,原来是乡村小舍,而且是哲学家隐居的乡村小舍。比如朱湘的十四行诗虽然句式的排列极其整齐,但他在诗中同样使用许多农村生活中常见的事物,用简单的意象处理戏剧性的人生题材,使其“建筑的美”显得更有生活气息和更耐人寻味,好象屋子里正在发生着严肃的人生行为,屋子外的烟囱还在冒着炊烟。
朱湘把民歌的美运用到诗的节奏、辞藻、氛围、格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闻一多的“三美”诗论,不仅使新诗作品简约明快,节制了情感,而且把新诗从闻一多、徐志摩很浓的文人气中解脱出来,拉进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强化了新诗的时代感,使新诗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除了“新月派”以上的三位主将,新月派其他诗人如卞之琳、何其芳等也在不同侧面丰富和完善了“三美”诗论,“三美”诗论成为指导新月派全体诗人创作的理论,并在群体的创作实践中成熟,这一诗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诗滥情和白话无味的问题。新月派的探索影响了同时代的现代派诗人和象征派诗人对新诗创作的继续探索,不断丰富新诗的表现手段,终于使新诗走向完全成熟并最终孕育出新诗创作的集大成者艾青。
(闻一多手迹)
[参考书目]
王光明 著《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公木 主编《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徐荣街 等主编《古今中外朦胧诗鉴赏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陈绍伟 著《诗歌辞典》(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黄曼军 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注】
1、本文已在别处发表,此系转发。
2、插图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插图。
(编辑:董尧、霜婵、丰渔)
(作者2019年2月在书斋)
【作者简介】董元奔,字固辕,号时雨斋人,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传统文化学者,网络知名作家。系江苏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机构独立创办人及教学骨干,因成就突出两度被省教育厅作为机关杂志封面人物进行报道,《中国教育报》、《中国考试》、《新华日报》均作了深度报道。曾服务于教育主管机关,期间参与《江苏教育年鉴》部分文稿撰写。学业主攻唐宋文学,涉文史哲诸领域。已发论文、随笔、诗歌等约百万字,其文史随笔或雍容华赡,或泼辣犀利,绝句则清丽润朗。曾有专著出版,有教育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主题征文一等奖,有文学论文获今日头条“青云计划”优质原创作品奖。
- 分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