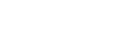《愚公移山》教学反思(2)
“直击中考”部分,我选择了2011年的两道中考题作为课堂练习:1,本文语言简洁,但又不失生动,请以“始龀,跳往助之”为例作简要分析。2.比较文中愚公之妻与智叟对愚公移山提出的看法的句子,说说有什么不同之处。在学生完成的期间,我走下课堂个别指导,并请学生起来回答。让其他学生总结他们回答的得分与失分。最后一同总结答题思路。切实切中中考。
篇三:钱梦龙:《愚公移山》教学反思
1981年4月初,杭州大学《语文战线》杂志社举办过一个小型的“西湖笔会”,与会者有刘国正、章熊、顾黄初、欧阳代娜、陈钟梁、范守纲、林伟彤、陆鉴三等语文教育界的名流,东道主是《语文战线》主编张春林君。我也有幸叨陪末座。笔会的主题是探讨语文教学的现状和未来。人数既少,兼以志同道合,笔会的气氛始终是愉快而融洽的。
当时的西子湖畔,正是早春季节,偶或还有春寒料峭的天气,但苏堤上的垂柳已经吐出新芽,碧桃似乎也已小蕾深藏数点红,孕育着无限生机。这多么像80年代初的语文教坛:改革的春风已经微微吹拂,不少改革的先行者正在进行着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人们似乎已经听到了“语文教学的春天”日渐临近的脚步声。但是眼前,毕竟春意还不太浓,要看到一个百花烂漫的“艳阳春”,还需要等待一些时日。西湖笔会在这样的早春时节,在这样的西子湖畔召开,确实引起了与会者许多联想,也平添了几许谈兴。
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的兴趣最后集中到语文课堂教学的改革上来。为避免空谈,又觉得应该作一点实实在在的尝试。于是决定从与会者里推出一人,借班上一次“尝试课”。教哪一类课文呢?大家又认为首先要瞄准语文教改的“死角”开火,于是想到了文言文。多少年一贯的“串讲”模式,在文言文教学中业已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似乎教文言文就得这样,舍此别无他途。大家希望“尝试课”教出一点新意,一改这种窒息学生性灵的刻板教法。这可是一件不太好干的活儿,由谁来承担呢?与会者中不乏教学的高手,事实上谁干都行,但张春林君提议:“这件事就交给钱老师,怎样?”一言既出,大家不便反对,于是在一片“同意”声中,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对文言文教学,我本有自己的主见,对普遍流行的“字字落实,句句对译”的传统教法,素怀“叛逆”之心,并曾为此作过长期的探索。因此,什么客套话都没有说,就欣然表示“愿意一试”了。当时定下的试教课文是《愚公移山》。事后春林对我说,当时定下这篇课文,他是有些担心的,怕我“创新”得太离谱,比如诱导学生去批判愚公“缺乏科学头脑”,称赞智叟是“智力型人才”,或提出“移山不如搬家”之类的见解,因为当时正有一些同志在报刊上鼓吹这类时髦的“新”思想。听课以后他放了心。因为我不仅没有否定愚公精神,没有削弱这篇传统课文固有的教育功能,而且把“文”和“道”交融得那样自然熨贴。他认为,传统课文被教出了新意,决定在《语文战线》发表这两堂课的全部教学实录,把它作为这次“西湖笔会”的实绩之一,也作为一份向全国语文教育界发出的“改革宣言”。
其实《愚公移山》这样教,在我,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我教所有的文言文,用的都是这种教法。早在1979年下半年,上海市郊区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在我任职的嘉定二中召开,全校老师都向校长们开了课,我教的就是《愚公移山》这一课,用的就是这样的教法。这堂课使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遍语文教师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并终于使我在1980年初评上了特级教师。因此,现在重教这篇课文,自然轻车熟路。不巧的是,当时正患感冒,嗓音严重嘶哑,到上课的前一天,几乎发不出声,守纲陪我到浙医大附属医院求医,他让我冒充杭州大学请来讲学的“教授”,才得到了一位已经不看门诊的著名医学教授的亲诊,而这位教授开出的药方,又是一种叫什么“散”的名贵中成药,医院里没有,守纲陪我跑了好几家中药房,才总算在一家已经打烊的药店里买到,时间己是下午6点多了。而第二天一早就要上课,真正可用于备课的时间,只有晚饭以后到入睡之前的那一小段空隙。好在我已不需要备课,否则真不知道第二天的尝试课会上成个什么样呢。
当时我担心的倒不是自己怎样教,而是学生能否适应我这种“不串讲”的反传统教法。因为《愚公移山》是初二的教材,而其时初二的学生已经学过这篇课文,因此只能借一个初一的班级。为这次教学提供班级的学军中学虽说是重点中学,但毕竟学生是初一的,他们入学以来只读过少量的文言文,他们能适应我的教法吗?
那天上课,为了保持常态的教学环境,听课者除了参加笔会的几位外,只吸收了少量当地和本校的教师。上课之前,因学生尚未看过课文,我稍作指导后先给20分钟时间让学生自读。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学生的兴趣被激发的时候,他们释放的潜在能量,比我们估计的要高得多。
“老愚公多大年纪了?九十岁还是九十不到?”
“参加移山的总共几个人?”
“愚公妻和智叟讲的话差不多,两人对待移山的态度一样吗?”
“愚公到底笨不笨?”
一个个有趣的话题激起了学生“投入”的热情。
“那个京城氏的七八岁的孩子也去移山,他的爸爸能让他去吗?”当学生一时不能回答、随即恍然大悟地叫起来“那孩子没有爸爸!”的时候,他们简直乐开了怀:想不到一向认为枯燥的文言文,居然可以学得这样开心!
始终在一旁听课的刘国正先生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记得我在杭州听梦龙教《愚公移山》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进入了‘角色’,同学生一起时而深思,时而朗笑,忘记了自己是听课者。其他听课的老师也有类似的感受。”
这次“尝试”的结果,虽非完全出乎意料,但毕竟有些喜出望外。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借班上课,也是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班级中验证我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次意义不同寻常的“尝试”。这次双重意义的“尝试”,使我获得了某种新的启示,再看西子湖畔的早春风光,似乎悟出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东西,却又一时说不清楚——只觉得我正在思考、探索着的某种教学理念,蕴涵着一股强大伯生命力。什么理念?
我不知道。既然说不清、道不明,就只能借诗的语言来表达一点朦胧的感觉:
二月东风似女郎,
飞红点翠写春光。
料应难染参差柳,
先试新梢几缕黄。
遥看苏堤上的早春杨柳,只是淡黄一抹,尽管参差“难染”,但终究会随着艳阳春的到来而垂下万条绿丝绦的。
“西湖笔会”以后,黄初以“江南春”的笔名在《语文战线》发表文章,介绍笔会盛况,文章标题就是《先试新梢几缕黄》。莫不是我的拙劣的诗句也唤起了黄初同样的感受?